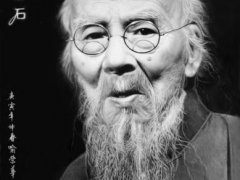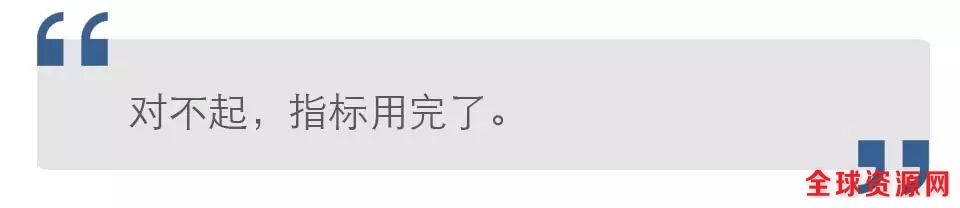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印第安营地》,写的是一个接产的故事。白人医生来到印第安聚居地,为一名难产的印第安孕妇接产,但意外地发现需要做剖腹产手术。因为没有带麻醉剂,医生只好在无麻醉的情况下,用一把大折刀做手术。孕妇的丈夫因为腿部有伤,一直躺在双层床的上层。在听到孕妇在手术过程中的惨叫之后,他竟然用刮胡刀自杀了。这个故事尽管惊心动魄,但在一向极度克制的海明威的笔下,竟像是一幅没有色彩的素描。
产妇的老公为何自杀?有很多说法。因为海明威一向用“冰山理论”写作,好事者于是开发出一种猜谜游戏,试图研究出小说中没有道明的潜在叙事。但我个人仍然倾向于认为,这个丈夫实在是无法忍受妻子正在遭受的痛苦,只好结束自己的生命。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逃脱现实的折磨。
绥德产妇马茸茸因为无法忍受待产的剧痛,在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跳楼自杀。当这个新闻开始刷屏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追问医院的责任,而是回顾一篇早年读过的小说。这种奇怪的举动,甚至让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印第安营地》和马茸茸的遭遇,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叙事,但当它们被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又说明了什么。我们早就习惯了日新月异的生活,我们热衷于讨论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发现,我们津津乐道于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的福利,然而,我们却一直都在忽略,人类繁衍这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似乎始终处于蛮荒而残酷的文明飞地上。就像一位产科医生所质问的那样,早就有了无痛分娩的技术,为什么我们还要忍受那样的痛苦呢?
没有一个男性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女性在分娩时遭遇的身心痛楚。一个孕妇怀胎十月、马上就要产下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本该满怀忐忑的喜悦才对。但就在这个大功告成的当口,马茸茸却宁愿跳楼自尽。她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告诉人们,有些痛苦的确是人类难以承受的。知名产科专家段涛告诉媒体,产妇感受的疼痛级别是正向分布的,大部分人感知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有小部分人生孩子是不痛的,还有一小部分人生孩子的疼痛是无法忍受的。也许,马茸茸正是最后那一小部分人,是产妇中的少数。当她的痛苦无法得到医生和家属的理解,她只能选择自我解脱。对于文明世界来说,这样的解脱,只能是一个巨大的嘲讽。
但如果把马茸茸的死完全置于一种形而上的语境中,就会减弱它的现实悲剧性。马茸茸两次走出分娩中心寻求帮助,最终还是没能剖腹产,原因究竟何在?什么样的力量扭结在一起,迫使马茸茸必须独自忍受痛楚?任何简单的归因,都很难令人信服。
对于产妇家属而言,顺产肯定是最优选择。经济花费比较少,怀第二胎也更方便。如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坚持顺产也算得上“人之常情”。但医院为什么也更支持顺产呢?其中的原因或许更复杂。有媒体通过检索公开资料发现,严控剖腹产率,已经成为某些地区卫计部门的重要考核指标。如果这个月的“指标”用完了,对不起,你最好还是顺产。当事医院是否受到这种“指标”的困扰,目前还不清楚。但一个更容易看清的事实是,医院在面对马茸茸多次自诉无法忍受时,基本上采取的就是一个拖字诀。院方事后的声明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产妇本人未撤回授权且未出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未获得被授权人同意,医院无权改变生产方式”。问题在于,疼痛中的产妇,怎么才能懂得“撤回授权”呢?医院准备了这种“撤回授权”的文件吗?
但医院在面对特殊情形时所表现出的迟钝,也并不能全然归咎于当值医生。由顺产变为剖腹产,其中包含了难以承担的风险。从目前的医患关系看,医生宁可事事都照着“规矩”来,也不愿根据患者的情况采取自选动作,因为一旦出现不可预料的后果,往往会给医院和个人带来巨大的麻烦。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关系一旦被扭曲,它往往会把每个人都置于困境之中。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有些现实问题“无解”。为什么如此无力?我能想得到的原因是,我们寻找答案的方向或许就错了。再好的制度,它终归是“死的”,它总也不能覆盖现实中的每个特殊与偶然。只有执行制度的人怀有爱与悲悯,只有每个处身于制度之中的人都怀有谅解与包容,制度才能发挥它的协调、缓冲作用,而不至于沦为推卸责任的工具。我们所要寻求的,或许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制度,而是价值观的统一。所有的撕裂,难道不都是价值的撕裂吗?
马茸茸的死包含着怎样的价值追问?也许是生命至上与女性权益。无痛分娩、剖腹产率、撤回授权、疼痛指数,所有这些术语都不该遮蔽最本质的追问:我痛得快要死了,谁能帮帮我?
(文/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