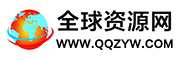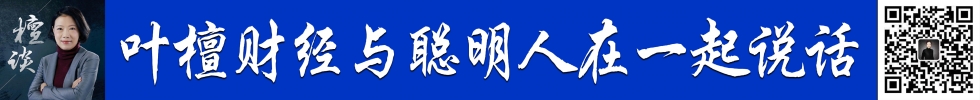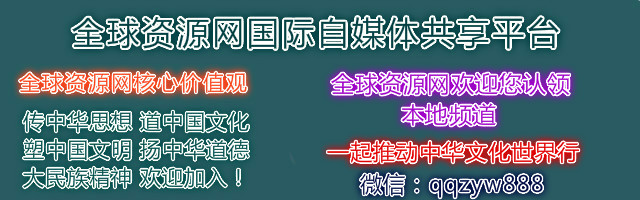滴滴还只是一个吸纳了风险投资人巨额资金的创业企业,而阿里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中可能是最大的单一构成部分,以及最大的增量来源,去年它的交易额超过了3万亿元,预计占到当年全部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
不过,这会提供另一种思考维度:即便政策层面阿里仍然拥有足够的博弈筹码,但逐渐主动向“后超国民待遇”转型也许更符合阿里的长期利益。当一家公司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又处于敏感的零售端时,它的未来也将越来越和这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密切相关。
因此,对阿里而言,从流量经济转向产业经济模式,真正着手构建有利于长远良性循环的生态,将生产率贡献上升到公司的核心考量目标,而非仅仅满足于眼前的规模和市值狂欢,以及沉醉于公关的“巧实力”,可能才是长期价值的关键,因为任何不利于这一指标的行为,最终会反映到长期业绩上,而投资不正是一项针对公司未来业绩的生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