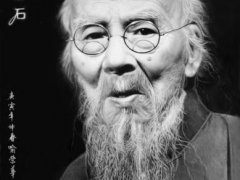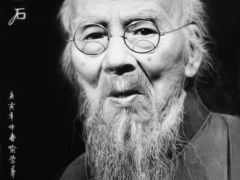在东保卫矿区里,老旧的宿舍楼之间是低矮的棚户区,旁边就是堆起的垃圾。(许晔/摄)
即便已经改制了15年,双鸭山人仍然习惯把煤矿公司称为“矿务局”。3月11日开始,数千名双鸭山矿工聚集在矿务局门前,要求龙煤集团支付被压长达半年的工资。他们还一度占据了铁路,导致北上的火车不得不绕道行驶。
有人坚持不用“闹事”来称呼这场聚集活动,因为“只是要工资,又不是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在官方的报道中,这次聚集活动被定性为“是在理性、温和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发生过激行为”。几天后,煤矿职工们陆续收到了工资。三个月的。
在双鸭山东保卫矿区,一位矿工允许凤凰网(凤凰网【严肃新闻】微信公号ID:Serious-News)拍摄他的工资条,用手指遮住自己的姓名,并拒绝了采访。他的职位是主扇司机,龙煤集团向他补发了2015年11月、12月和2016年1月的工资,共计2924.91元。取暖费仍然没发。另一位矿工老孙在电话里说,他也收到了3个月的工资,除了一个月是足额发的,剩下两个月加起来只有1500元左右。
东保卫矿建于1983年。一位1998年退休的矿工说,当年建矿时有2万多人,如今这里只剩下了7、8000人。这座矿距离双鸭山市37公里,工人们基本上都住在矿区里。住宅区的建筑大多建于上世纪80年代,涂成黄色的墙壁斑驳发黑。楼房之间是一排排低矮的棚户区,生活垃圾堆在宿舍楼旁边,开春后的雪开始融化,一脚踩下去是松软的黑色泥土、腐烂的菜叶和动物的粪便。矿区被围墙圈起,如今大门前停着一辆警车。矿区里的人说,前几天,门前的守卫拦下了一位外国记者,把他关进了屋子里,不知道是美国的,还是俄罗斯的。

贸易街“改革开放”的门柱上,贴着出租、卖楼的广告。(许晔/摄)
商业和资金正在迫不及待地逃离。在宿舍楼下、商业街的店铺玻璃上、贸易街“改革开放”标语的门柱上,到处都贴着广告,内容简短直接,没有任何天花乱坠的形容词:“卖楼,48栋5单元5号,137XXXX3091”,“楼房出租,出卖,150XXXX1048”。这里的房价在2012年能达到每平米4000多,如今已经跌至每平米1000多,仍然无人问津。“这些房子都闲置的,没人要。”
一家药店在玻璃橱窗摆出了广告板,标明7种药品的价格,底下用红色笔写着:“现金购药。”矿务局的医保卡已经无法在药店里使用,即使只是买两包价值1块5的棉签。这家药店的老板称,矿上欠药店的钱已经有一百多万。
“不退休的还不如退休的。”已经退休的工人们说,他们每个月的退休金可以准时到账,虽然取暖费还是拖欠许久。“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就混一混了。三个月三千多块钱,现在养一家子够吗?”在东保卫矿去往双鸭山市的巴士上,一名矿区职工说,他的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在双鸭山市的一家公司当会计,让他没了后顾之忧,“但有人家里还有孩子上学呢。”
欠薪
双鸭山市的群体上访,不是东北首例,也绝不是最后一次。2015年4月,同属于龙煤集团的鹤岗就曾爆发过数千名矿工上街讨薪事件。

萧条的商业街。在2012年煤炭行情好的时候,这里的歌厅、KTV很是热闹。(许晔/摄)
煤炭行业在2012年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期,步入了衰落状态。煤价下跌带来的萧条肉眼可见——2012年在东保卫矿商业街热热闹闹的KTV、歌厅、舞厅,在4年后几乎全都黄了,只剩下破败发黄的塑料布广告。在2012年,一个刚进矿里的工人每月工资可以开到5000左右,但在2016年3月,这些工人要通过上街和堵铁路才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酬劳。
双鸭山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曾在宝山区的矿区干过半年,那是煤炭行业比较景气的2012年。他当时没有办全所有手续,就开始下井干活。曾有一次井下塌方,身边的同事被石头砸死,赔的挺多。“其实那个时候在矿里干活也不算很累,每天工作8小时,下井上井就得2个小时,在底下工作5、6个小时就下班了。”
双鸭山事件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一篇文章又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之中,在文中,她写道:“在煤炭工人的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这篇文章写于2013年,正是煤炭行业衰落拉开序幕的时候。
煤炭、钢铁的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跌带来的经济萧条,让人联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当时下岗失业的3000万人中,有四分之一在东北。人们恐惧于失去生活的来源,欠薪、上访,在东北各地都在上演。

停产的钢铁厂。(许晔/摄)
在吉林辽源市,2007年接手辽源钢铁厂的吉林鑫达钢铁公司已经停工2年了。这座钢铁厂像是头笨拙的机械巨兽,沉默地卧在东丰县横道沟的田野之间。有些耕地被征收了,盖了新城。失地的农民便去钢铁厂上班,可工资已经被拖欠两年了。工人们2014年1月罢工,10月投诉,2015年8月投诉,可工资还是没发。“钢铁不值钱了。现在一斤废钢2毛多,一斤废纸还4毛多呢。”
他们的上访被扼杀在萌芽里。一位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回忆说,当时运管所、公安在路口拦着,能带人进这里,出来只能是空车,“否则就要扣车”。2015年8月13日,这家公司被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原因不是欠薪,是欠了一家煤矿,一家商贸公司和一家银行的钱。
重工业企业曾是东北三省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在效益不错的那几年,龙煤集团曾每年为黑龙江贡献数十亿的税收,但现在它们成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据《经济参考报》报道,龙煤集团一位高管称,前些年煤炭效益好时,省里从集团拿走十几个亿用于公路建设,现在煤炭行业不景气,只能靠向省里借钱发工资。
“如果它们破产倒闭,可以把资产核算给这些工人发工资啊,他们愿意让这些企业破产吗?”
“他们需要矿上给他们交保险啊。我现在是自己交,以后这些钱还能到我手上,如果矿上倒闭了,他们就得自己去交养老保险,所以还是有些人不愿破产倒闭的。”那位曾经做过半年矿工的出租车司机回答。
“去南方”
像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欠薪的工人们甚至已经无法承担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建立在充盈的可支配收入基础上的商业迅速萎靡。在东保卫矿里,一家店铺门前已经挂出了“店小利薄概不赊账”的牌子。一家超市老板说:“之前他们还有(每月)开支几十块钱的,就能买点米,不赊账怎么办?”
在产业结构单一的东北,假如离开国企的庇护,矿工们很难在本地找到大量替代的工作机会。相较于因煤建城的双鸭山,位于长春附近的辽源似乎幸运得多。这座城市曾在80年代被称为“东北小上海”,拥有比较完善的轻工业系统,除了生产煤炭,这里还会生产袜子、内衣、半导体。2005年后,国营针织厂的“遗产”被民营老板们接收,他们雇用了拥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购买机器,创办了袜子厂。当地的煤矿已经开发了一百多年,逐渐枯竭,矿务局也开始面临发不出工资的窘境。一位袜厂的老板说,他们现在基本可以给工人开到每月2500元的薪水。

辽源市经济开发区的电子商务区。整栋大楼空荡荡的,标语严肃得像是备战高考的高三教室。(许晔/摄)
计划经济的烙印依旧挥之不去。辽源市财富大道上有一栋高楼,是经济开发区的电子商务区。这位袜厂老板说,政府曾经想让每家袜子厂在这里开个网店,可他觉得没必要。“我们只要管好生产研发就好了,电子商务就让专业的来做。也不能我们从头到尾全部包了吧。”
电子商务区的楼里空荡荡的,有些隔间成了袜厂的仓库,有些空着。大楼里贴着横幅和标语,严肃得像是备战高考的高三教室:“开放平等协作分享”,“腾笼换鸟空间换地机器换人电商换市”。楼里三三两两的行人走过,没给这些标语施舍半点目光。
大楼前的电子屏一直不断闪烁着,有时是蛋糕店的广告,有时是袜园的宣传口号。电子屏的中部始终显示着:“未连接上硬件”。
上述袜厂老板说,受到经济大环境影响,今年开始,袜子生意也不好做了。“往年我仓库里最多只会堆一半吧,现在你看,这全是堆的库存。我们原先预计淡季会从4月开始,没想到来的这么早。”他抱怨陈旧的官僚给他们带来的阻碍:“以前是给钱办事,现在不敢收钱,也不办事了,这还不如以前呢。”
2015年1月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对东北困境分析道:“东北的经济结构在过去十年间却进一步失衡了:其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依赖于投资与制造业,国有与私营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向采矿业、重型装备制造业和建筑业倾注资金,而这些恰恰是同当前低迷的房地产市场高度关联的。”

荒无人烟的辽源市南部新城。因为路修得好,这里成了当地居民练车的地方。(许晔/摄)
在辽源,通过当地人的介绍,凤凰网走访了包括辽源市经济开发区在内的5个大型项目,3个在城区,2个在远郊的东丰县。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经济开发区是5个大型项目中唯一一个还在生产GDP的地方。剩下的4个项目,只有工地,没有工人,除了风声,听不到其他声响,荒得如同一座空城。
按照《吉林日报》2012年11月的报道,位于辽源市的南部新城“规划用地面积13.36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约为136亿元,规划建设期为5年。南部新城建成后,可以实现8万户居民入住,成为容纳24万人口的现代化高档居住社区。”但在2016年3月,这里成了当地居民练车的地方,因为路修得好。“可以改名为南部驾校了。”一名网友在辽源贴吧里说。
而在辽源东丰县的新城里,东丰二中旁的餐馆老板并没有觉得新城建立有带来任何商业好处。“这里什么也没有,买什么都不方便,买菜得去老远的地方。我们生意不怎么样。新城这里很多都是陪读的家长,他们会在家给孩子做饭。”“35岁左右的都想出去,去平台更好的地方。我们是比较老的人了,也不会电脑,出去不好找工作。”
年轻人正在离开这片土地。无论是边境小镇,还是煤城,年轻人都在追逐着财富和机会,向市场经济更发达的地方流动,或是中国的南部沿海,或是一水之隔的韩国。根据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东北劳动力净流出规模已达200万人。“念完大学的人都不愿回来。”
在鸭绿江最上游的长白县马鹿沟镇,年轻人去韩国或俄罗斯就可以挣上每月6000-1万的工资,他们的离开也让边境小镇的防守变得格外孱弱。在外媒的分析中,这成了中朝边境多发越境杀人抢劫案的原因之一。而在辽河源头的辽源市,一位基层公务员说,他给儿子最大的目标是出国,最次也要离开吉林省,“我们已经就这样了,他还有希望。”
春节之后,很多东保卫矿的年轻人就离开了这个衰败的矿区。“没有希望了,年轻人都走了。”一位退休矿工在墙边筛着土,身后是亟待出租和售卖的矿区宿舍楼。
矿工老孙的儿子也是矿工,他还在等待龙煤集团第三批职工分流的消息。在签完分流意向书之后,矿里就不再给他发工资了,新的职位仍然没有着落。如果还没有消息,老孙说,他们就考虑让孩子去南方了,“毕竟他还年轻。”
(凤凰网 许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