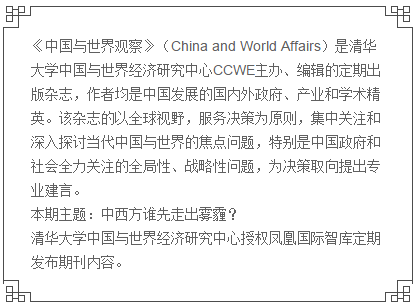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摘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启发和引导了良性资本主义的出场。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导致自己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的脱序。中国如何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开启自我批判的空间,直面制度缺陷并进行制度改革,从而向资本主义制度那样获得脱胎换骨的契机,是走出“重霾”的前提。
2008年,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陷入困局。跟着爆发了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缺陷的社会浪潮,以“资本主义危机”为论旨的著述,铺天盖地;旨在挽救资本主义体制的制度改革尝试,也相应出台。效果,似乎不是那么明显。
2008年,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困境。但因为中国政府4万亿的救市举措,让中国免于即时陷入经济危机的风险,并且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经济景象。于是,国内有不少学者盛赞“中国模式”,西方国家也有人夸奖中国的及时应对。以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成为被人称颂的市场替代性模式。
问题来了。其实中国并没能彻底作别经济困难,而是成功延后了经济困难爆发的时间。当4万亿救市措施发挥的经济效用迅速衰减以后,中国的经济困难愈见明显地呈现出来。只不过面对困难,政府与社会人士要么羞羞答答承认,但乐观展望前景;要么明显承认困境,但着重表达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因此,社会公众对中国面临的经济持续发展困难的认知程度,明显不够。不过确信无疑的是,困难还真个是狼来了。
恰当此时,中西方国家都在尝试种种克服困难的举动,前景如何,有待观察。但已经呈现出来的两种面对困难的态度,却让人忧心克服困难的最终结果,可能出现巨大差异。西方国家的权力部门,在强大的社会反思面前,做出了种种自我调适的举动。
一方面,强大的社会反思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社会清醒的自我认识、自我批判能力。资本主义一来到世间,就承受着天生左倾的知识界的严厉批判。这种批判,既有致力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社会主义、温和社会主义者,也有致力修正和改良资本主义、但捍卫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辩护士。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受到的批判,比资本主义受到的赞美,要多得多。资本主义一直就在批判中发育、发展、壮大和重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批判的活力,似乎来得更猛。尤其是对市场秩序的不信任与拒斥,和对国家权力的高度期待之论,携手出场,让人不仅看到西方国家视市场为金融-经济危机罪魁的一面,也看到西方国家视国家权力为拯救经济发展良方的一面。传统左派经济学家对之的阐述之多,不在话下。即便是在1990年代为自由民主终结了历史而欢呼的右派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对强国家表达了强烈的期待之情,以至于人们断言福山的立场变了。由此可见西方知识界自我批判的强度。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权力当局,也采取幅度大小不同的制度调整。尽管这样的调整,让西方国家呈现出左右两个极端的变化:左的方面,即使福利国家遭遇了明显困境,社会公众却要求更多的福利。于是希腊危机更加重了国家危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更为繁重的福利负担。右的方面,出现了市场化的辩护倾向,对政府按照行政意志调节市场的举动大加抨击。换言之,2008金融—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对市场失灵、政府失效有了更加深刻的对应性认识。单纯强调政府或市场某一方面的作用,都不再能说服人了。
反观中国。2008年以来,国家权力方面确实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收效是显著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快的,因此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问题有显隐两个方面:显性的问题是,经济周期的表现越来越明显,政府调节能力的施展空间越来越窄了。隐性的问题是,中国在为自己的发展模式自豪和辩护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另一重任务。
这是需要分别认知的两个问题。从显性的问题看,中国长期实行的需求侧改革,形成了经济迅猛发展的三大动力:投资、内需与外贸。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的过度投资难以为继,内需在想方设法之下很难拉动,而外贸因于经济政治交错因素难有明显起色。于是,供给侧改革随势而兴。但真正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严格约束政府控制经济的行动。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流于政府调节企业的市场供给,因此有一种国家带动发展模式的换汤不换药意味。由于政府手中调控经济的手段明显短缺,市场对政府调节的反应趋于迟缓、甚至趋近反向作为。因此,中国政府面对眼下的经济困局,运用行政权力调节经济似乎不再熟稔于心。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随之增加。当下的中国经济,究竟是经济周期的作用,因此一个时段过去,好景必定重来呢?还是经济—政治结构性问题的集中表现期已至,故而必然经历一个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才能走出困境呢?似乎谁对之都没有一个信心十足的答案。如何在强势的国家带动与市场的微观改革匹配模式之外,开辟一条创新性的经济发展道路,明显已经成为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改革红利千万不能再处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态。这对中国绝对是一大考验。
从隐性的问题看,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新胎萌动和甫一降生,都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为意识形态和制度建构前提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固定思维模式中,既没有给社会主义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留下解释空间,也没有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遭遇相同难题留下制度余地,更没有给社会主义起伏跌宕的运行进程留下回环天地。因此,不论处在什么经济—政治状态中,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硬性为自己的全方位优越性做无条件的辩护。这无形中将问题悬搁了起来,加强了认知问题的难度不说,更将问题隐匿起来,让其难以捕捉,遑论加以解决。当下学界一些人士忙于批判和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纰漏,强烈暗示、甚至是明示人们,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这在有形无形之间,将中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了,让决策当局掉以轻心,一旦真正遭遇经济危机,局面难以设想。尤其是人们近期谈论颇多的“言路”问题,也对中国构思出路形成压力。这让中国解决其经济—政治难题的想象力明显下降。
中国与西方国家面对危机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对比:西方国家在内外的压力之下,策略性修正与结构性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国顶住内外压力,对自己的压力承受能力颇有自信。目前尚不能断言中西方国家走出困境的前景究竟会是如何,也许自信心是走出困境的重要精神支撑,也许有条不紊的改革才是走出困局的关键棋局。但从面对困境的姿态本身上讲,仅有改革举措显然不够,而仅有自信心也未必敷用。西方国家需要对自己面临的制度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层理论反思,中国需要在自信心之外强化制度反思能力、自我批判能力、自主超越能力。在面对困境的竞争性对局中,谁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双重先机,谁就能够率先走出目前的困局,取得新一轮制度竞争的决定性优势。
目前的态势有待观察,回顾历史便富有教益。在国人最执着关注,并成为我们制度运转的惯性政治思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性理念中,究竟哪种制度更优胜,在中国俨然是一个关乎政治正确的大问题。表态是容易的,当然是社会主义胜出。但确认事实是困难的,因为两种制度一直是现代性的两面,总是在相互伴随的过程中呈现其制度竞争力。
两种制度的竞争史,已经呈现出几起几伏的竞争曲线: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之野蛮,让社会主义在对其道义的批判占尽道德优势。这成为社会主义得以修正资本主义的第一波浪潮。但占尽制度实际优势的还是资本主义。以20世纪早中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建立,宣告了这一竞争的胜利一方是社会主义。道义的批判,成为制度的替代。这是两种制度竞争的第二波浪潮。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两种制度的竞争陷入胶着状态。社会主义阵营尽管分裂了,但却成为后发国家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辩护,与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运作图景的、具有鲜明对比效果的两幅画面。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守势之强,促人展望后资本主义世界景象。资本主义陷入了自我质疑、批判和修正的窘境。这是两种制度竞争的第三波浪潮。但到20世纪后期,两种制度的竞争态势,出现逆转,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资本主义国家再次胜出,福山宣告“历史终结”了。这是两种制度竞争的第四波浪潮。直至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形势似乎颠转:资本主义再次遭遇危机,社会主义似乎又成为解决危机的答案。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遭遇困难,其宣告资本主义灭亡的调门,明显不如20世纪50年代。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辩护,却嗓门不减。这是两种制度竞争的第五波浪潮。
将两种制度的竞争性调适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进取与退守、自辩与调适、主动与被动的显著差异。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启发和引导了良性资本主义的出场。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导致自己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的脱序。中国如何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开启自我批判的空间,从而向资本主义制度那样获得脱胎换骨的契机,恐怕是走出这一波发展“重霾”的结构性调适前提。
目前的中西方国家都还处在经济—政治困局之中,面对困局的姿态、决策与举措,会决定性地影响双方竞争性对局的前景。一方面,前途未卜,需以理性和审慎的态度观察、应对。另一方面,观察、分析与抨击对手的热情,一定不能压倒直面自己问题的动力。换言之,对于自己各自的问题,认真面对、严肃解剖、批判反思、改革制度、寻求实效,恐怕是任何一方走出困境需要确立的不二进路。
倘若我们中国先行确立这样的进路,一定会率先走出这一波重霾。这是我的强烈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