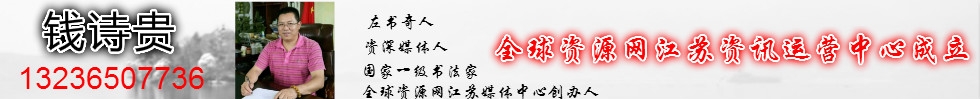老家农事
天特别的热,多数人是以避暑为主,而农民却要下田劳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的极是。
我在农场生活了十八年,父母皆是农民,我也当了半年农民,对农民的苦多少了解些。说到农事,只能知道大概了。

老家靠海边,许多年前实际上是海底。海退人进,开荒种田,居然成了江苏最大的农场,人口三万多人。
因为是盐碱地,不改造很难长庄稼。小时候,太阳一照,一股白茫茫的蒸气漂浮在地面,可见盐分多重。
许多开好的田不长一粒庄稼,只长猪能吃的野草,泥巴一层层地翘起,手轻轻一揭,如同米饭锅巴一样。

为了改造,农场种了大量田青,据说专门用来排碱的。田青长得很高,孩子钻进去根本发现不了。
因为找到了玩处,放学后的孩子们分成两派,互相捉迷藏,开心的不知吃饭。
家长很着急,弄不清孩子躲在什么地方,只能站在田青地头高声喊叫。害怕被打的孩子根本不敢吱声,一溜小跑抢先回家了。

盐碱地草易长,庄稼往往没草长得快,农工除草的任务很重,几乎天天带把镰刀,逢草必割才行。
芦苇随处都能长,农工又恨又爱。端午节到了,芦苇叶子又肥又大,是包粽子的上佳材料,许多外地人吃了农场的粽子后,都说好吃,便朝亲戚要起芦苇叶子来。为此,当地人吃过粽子后,芦苇叶子并不扔掉,要打包晒干,挂在屋檐下,以备亲戚索要。据说陈的芦苇叶包粽子更香。

芦苇是编席的上等材料,家家床上都铺着芦苇席子。农闲时,妇女们忙着编席,好偷着卖给信用社,换些日用品。那时是不允许私自买卖的,好在都是左邻右舍,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农场还有一个几千亩的芦苇荡,里面有野鸡、野鸭、野兔等,打猎爱好者只要进去,保准满载而归。
遗憾的是,农场当权派一声令下,把芦苇荡开成了鱼塘,野生动物再无踪影了。现在想来,这些当权派其实是农场的罪人,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农场大概能生产小麦、稻子、棉花、高梁、玉米、大豆及蔬菜等农作物。
水稻引进迟,但印象很深,谷雨浸种,立夏落秧。秧田要先放水,用木板把地面磨平,再撒上种,叫育秧。种子上用灰和粪盖,等长到五六寸左右,农工开始拔秧。
插秧前,用犁先耖下田,灌上水,再耙平土,然后开始插秧。

记得插秧时天很热,我放农忙假,曾插过半天秧,后背被晒脱一层皮不说,还被几只蚂蝗盯住了,至今想来还觉得鸡皮疙瘩暴起。
不过插秧时有吃的,是队里大锅饭,一碗米饭,一碗包菜,这大概是我人生第一份酬劳。

插秧不到十天,就得下田薅草了,不过野草薅不尽,薅之又生,只得不停地薅。一时间,稂莠荑稗杂其稻出,薅后茎叶又长,苦了农工。终于到了收稻时,基本上以镰刀收割为主。收获后,赶种晚麦。种好后,场上打稻。当时一位叫倪排长的,刚摸到插头,即被电击中,倒地半时才苏醒过来,吓得众人直打哆嗦。

开春到了,睛天时修整水渠;雨大时,开沟放水,罱泥拌草,农工之勤年年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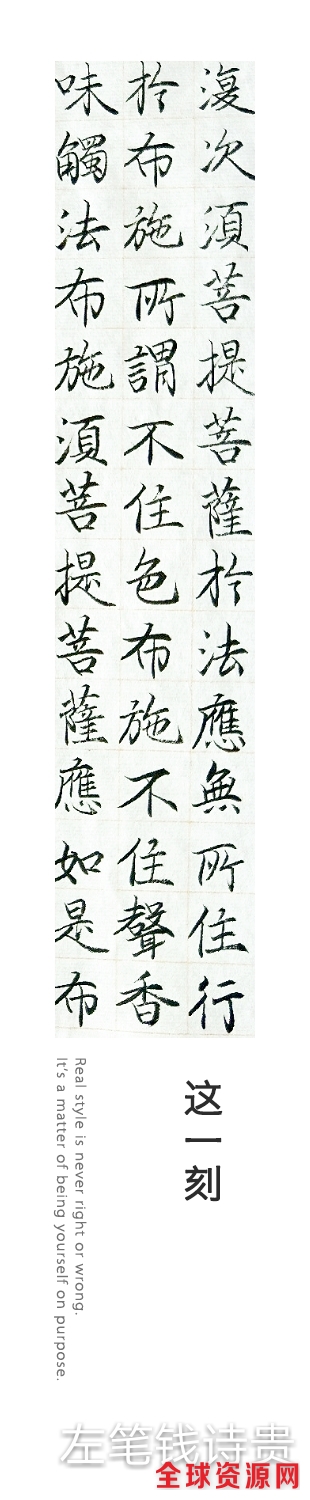
我做农民时,先被分配看青,以防有人偷庄稼。一同看青的有两位南京知青,一姓吉、一姓刘。正忙于调回南京城,故心不在焉,常躲在树林里纳凉、侃大山、下棋。
所谓棋,并无棋子。只需在地上划个棋盘。横六道,竖六道即可,每人用泥巴或石子当棋子,分别在交叉点上摆棋,只到一方把对方棋子吃光为赢。我是个中高手,常把对方杀的弃子投降为止,这种棋有个名子,应该叫六路州吧?
看青结束后,又分配我看棉花,要住在生产队队部仓库里。仓库里有口棺材,当时并不害怕,照睡无误。装棉花要有专用包,由我保管,谁知越来越少,队里要找我赔。
正为此头疼时,一纸调令,我进城去了,自此告别了半年农民职业,告别了家乡。(钱诗贵丁酉日记)